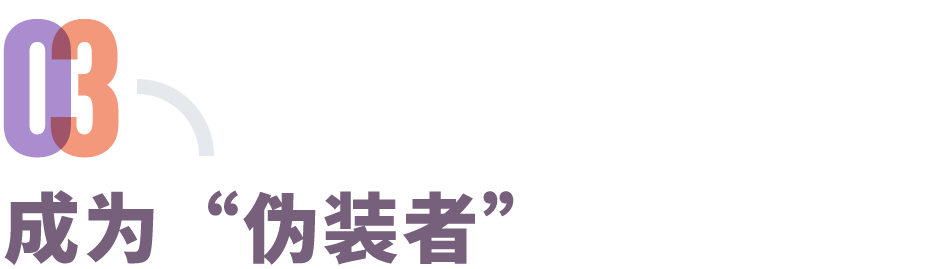作者:
张心佩是以理想主义的姿态成为一名人民教师的。她在河南一所小学工作,教龄十余年。采访她那天刚好是立冬。若是刚大学毕业,张心佩会想,这一天,她要跟学生们讲讲立冬的知识和诗句;要赶上下雪,就带全班去操场上打雪仗,观察雪花的形状,摸一摸雪的触感。
但现实中,张心佩的立冬是这样:除了两个班级的语文课,批改作业和备课,她还要写一篇活动总结,收集观看直播课的照片并上交,安排家长在校门口值岗,完成一份调查问卷(她来不及细看,胡乱填了答案),处理家长的各种提问,准备公开课……
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些年的工作感受,张心佩会答:“一年比一年压力大,一年比一年任务重。”
去年5月,一篇《只有畜牧局没给老师布置任务》的文章在她的朋友圈刷屏了。文章总结了教师们所面临的各式的非教学任务:扶贫、反诈、消防、防溺水、防欺凌、防火灾、交通安全宣传、文明城市创建……每一项,张心佩都再熟悉不过——它们至少占据她60%的上班时间。
距离那篇文章发布一年半,10月27日,郑州市管城区一名00后女教师自杀。她成为教师不过一年。那份由家属提供的遗书记录了她最后的发问:“什么时候老师才能只做教书育人的工作?不幸福的老师怎么能教出来积极乐观的孩子呢?”
她不是第一位提出这个问题的老师,也不是最后一位。
张心佩明显察觉到,“非教学任务”,正在入侵她的教学时间。
不久前,张心佩的学校办一场大型活动,大部分老师被借去布置会场、给学生化妆。学校通知,每个班只需保证一名老师在岗。也就是说,“从早到晚全是一个老师上课”。
另一种让教师们草木皆兵的是各主题艺术节。每个班级都要“像布置婚礼一样”装饰教室,排练节目。张心佩带低年级,孩子们什么都做不了,最后——装饰品是家长集资买的,教室是她掏空心思设计的。学生们只需在领导参观环节积极表现,像一颗颗聪明的小糖豆,活跃又听话。
活动结束后,她还得写宣传稿。不像写感想可以应付——她和同事常去百度文库上搜一搜,改一改(“哪个老师没有百度文库会员?”)——宣传稿比较难写,通常得花上一两个小时,还要配图,反复修改。稿子最后交由报社发表,她被光荣署上:通讯员。
“现在老师个顶个出去,干啥都会了,连策展我们都会了。”张心佩自嘲道。
公开课也占据了相当精力。这在张心佩眼里,是最装模作样的课,“整一些你平时永远不会用到的环节,永远不会说的话,然后演一下,大家再点评一番”。那些环节包括:花哨的板书,精心的道具,别出心裁的师生互动。有的老师会提前排练几遍,学生像是配合演出的NPC。
张心佩还会收到要求教职工点赞、投票的任务。她从不关心要点谁的赞。总之,赞就对了。
还有更多的非教学任务,瞄准了校外的家长。线上讲座、学习答题、视频资料、纸质资料、调查问卷……
检查任务也五花八门。有的要求家长看,有的是学生看,有的是家长、学生一起。全班50多个同学的家长得一一拍照,证明“真的看了”,再由班主任上报到全校的截图群。集不齐照片,办公群就会一遍遍@班主任。
年深日久,张心佩已经对排山倒海的手机信息产生免疫了,它们激荡不起任何波澜。那个充电的方块像是她身体器官的外延,而她是台冷漠的主机,机械地迎合外界对她的期待。
和张心佩一样,陈瑶也在被非教学任务“填鸭”。她是一名中学班主任,讲话时伶伶俐俐,有股南方女孩的俏皮劲。尽管当初冲着安稳才来当老师,陈瑶抱着极高的热情投入其中。她家离学校不过几分钟车程,还是选择住在学校的8人间宿舍,以便处理突发事件——比如半夜送生病的住校生去急诊。
陈瑶形容自己是上级部门最喜欢的那种得力干将:负责,有干劲,没有拖延症。可她的上进心正在被与教学无关的事情磨损着。
有次,她花了一个多小时为领导做演讲PPT,活动却没了下文。
另一次,学校迎检,让她提交今年写过的所有宣传稿。她只留存了草稿,硬着头皮交了。检查顺利过关——“根本没人细看”。
还有一次,教委发来一份PPT,要求师生认真学习。陈瑶打开PPT,除了第一张封面,后面全是乱码。但她还是遵守要求,让全班摆拍了一张集体观摩的照片交上去。
她忍不住感叹,“学校好像变成了一个社会管理的部门,不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了”。
在这种氛围下,家长和学生越来越像一种“资源”。陈瑶产生这种想法时,自己也感到吃惊。一回,学校群里发来一条链接,让班主任通知家长完成。落实下去后,家长向她投诉,怎么是卖东西的广告?陈瑶至今不知道是谁下达的命令。
“过去学校接收上级文件最多的是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文件,现在90%以上的是关于非教学任务的文件。”一本书写教育现状的图书《县乡的孩子们》总结道。
这本书的作者之一,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、中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雷望红。过去六年来,她在中国开展县域教育的田野调查。据她观察,一线教师关于非教学工作的抱怨声在2017年时就存在,此后逐年增加。
“中层干部和班主任是承担形式主义工作最多的群体。”雷望红对凤凰网说。
2021年,雷望红去江西某地调研。当时的座谈会上,一位小学中层领导倾诉时眼眶红了。他说自己经常加班到凌晨,就为了整理非教学材料。连动手术也只敢休息两天。
那位老师说了和00后教师遗书里同样的话,就想安安静静地教书。
作为一线教师,张心佩承受的压力是双重的,一重来自“上级”,一重来自家长。她也越发觉得,在多方关系中,老师的地位正在下陷。
有一次,张心佩路过学校球场,一只皮球朝她飞了过来,恰好砸中她的平板电脑,屏幕碎了。张心佩联系了学生家长,对方反问她,为什么学校不在球场外加固一层防护网?
校方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息事宁人,张心佩负责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,“不能让家长投诉学校有安全隐患”。
至于碎掉的平板电脑,无人理会。

类似的情况陈瑶也遇过。班里一个学生的手机在学校丢了,家长找到校长,校长推给年级,年级推给保卫科,保卫科让陈瑶写了一份情况说明。最后,陈瑶赔了学生200块钱。
陈瑶渐渐觉得自己在学校孤立无援,“发生了任何事情,没有一个人会站在你这一面”。可是这种话,她只敢跟家人、朋友倾诉。
调研中,雷望红有一个发现:不论学生在校园里发生什么情况,人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问责学校和老师,“就算学校在落实各项政策时,是合法合规、程序合理的”。
如是这般,那些冗繁的非教学任务——诸如坚持不懈地“写材料”,虽然是一线教师们沉甸甸的日常负担,但也成了高压状态下,一种保护自我的手段。
陈瑶的学校曾要求学生们手写一份“手机保管书”,表明是自愿带手机到校,并交由班主任保管的;等陈瑶带新一届学生后,她学会了使用同样的方法保护自己,于是让学生们写了第二份声明:学校不允许带手机,如果带了,丢失自负。
“现在的确出现了官僚化倾向,每一层都在想着避责,都要通过程序、规范、材料来规避自己的责任。各层级的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,考虑的不是目标本身,而是能否实现自我保护。”雷望红无奈地说。
占去老师们很大精力的是学生安全相关的材料,这也是形式主义的重灾区。
雷望红记得,从前一次调研中,有老师办公室里摞了一摞A4文件盒,里面装满了校园安全的文件,足有半个成年人那么高;
今年上半年,在湖南某学校调研时的雷望红见到离奇一幕:老师们聚在一间会议室,争相抄答案——那是一份防溺水的问答卷。老师抄完,再教学生抄,确保每个人都抄对了。
“我就问他们,有没有意义?校长可能担心犯错误,他说,还是有意义的。”电话那头的雷望红哑然失笑。
甚至,很多一线教师已经训练有素,达到了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境界:任何活动举行完毕,即便没有人要求写总结,他们也会主动写一份材料——以防年底检查时被人突击点名。
张心佩在班上挂着两张课程表,一张是真的,一张是假的。真课表用来上课,以考试科目为主;假的用来应付检查——印着张心佩从来没听说过的课程,例如“实践课”、“特色课”。
添加假课表的那天,有孩子问她这是什么。张心佩感到尴尬,又不想撒谎,只好糊弄道:“你别管这个。”
张心佩越来越觉得,教师和“地下工作者”有异曲同工之处。那些可能会留下把柄的(比如周六违规补课)、让人望文生义的事情,她从来都是电话通知,不敢留下文字痕迹。
老师对待家长如此,校领导对待老师也如此。“有时候学校通知一些事情,不给我们发信息,会让我们紧急去开会,当面说,出了这个屋就他不认了。”
比如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。老师们只会收到几点几分到会议室集合的信息,然后领取试卷,临时开考。卷子是不准学生拿回家的,所有人都在假装没有考试发生。
——不过,如今在学校,这被称作“学习测评”。按照教育部政策规定,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。然而在河南这样的高考大省,不考试,家长也会投诉。
这种“伪装”甚至蔓延到学校在面对监管部门的时刻。
之前,有督导组来张心佩的学校检查,随机抽选班级,安排学生做调查问卷。题目例如,老师是否推荐你们上辅导班,是否强制订阅教辅资料。
为了避免学生们“惹是生非”,有的老师不得不引导学生,“好好想一想,填哪个选项对咱们学校好,对咱们班级好?”
终于,张心佩的一位同事,在不堪重负之下,假扮他人举报了学校,说学校非教学任务过多、周六还在补课。
没人知道举报者究竟是谁。后来校方连开数次大会,领导要求每个老师站起来发言,对举报者说点“心里话”,像是玩一场真人版的“谁是卧底”。
张心佩打心底佩服那个同事的勇气。
但行动上,她选择配合会议精神,她站起来说:“如果你对学校有意见,也应该关起门来,内部解决。”
虽然“内部问题”层出不穷,真正的问题根源,却并不囿于教学系统内部。
在凤凰网采访的几位一线教师的描述中,很多任务都是“上面”布置的,经由学校教务口、办公室、后勤处或团委等安排下去。
问起“上面”究竟是谁,她们表示:这不好说。
《县乡的孩子们》一书中提到:“大量非教学任务进入学校,是上级政府强力推动工作落地的结果。”
“各个部门对校园的渗透越来越普遍了,每个部门都有相关的活动,每一项活动又要求得极其细致。”雷望红说。
雷望红曾问过一位县领导,为什么政府部门要将工作安排给学校,能不能让学校减负?
县领导答得诚恳:“现在县里的很多工作都必须集中全县的力量去解决。如何高效地解决?只能通过高效的组织来完成。”
学校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组织。雷望红解释说,学校是高度组织化的机构,分工明确,容易找到责任主体;又是高度动员型的组织,师生服从安排,“动员能力比其他组织强得多”。
由于各项工作都要考核排名,教育局会将各学校完成某项任务的结果,排名发到全县的校长群里。没有点名,没有批评,但谁都能看到,静静的表格上,排名末尾的学校名字被标红了——校长面对上一级时的压力,和小学生别无二致。
雷望红又问县教育局的领导,能不能在教育局这一层将非教学任务过滤掉?
“很难。”对方说。
因为县教育局也有上级领导,某些工作完成不好,拉了全县的后腿,就会影响县城在全市的排名;况且,教育系统也得靠其他部门协同,今天你拒了别人,下回别人也不会太赏脸。
于是压力经由巨大的行政系统链条,一层层向下传导,直抵末端的学校。
在张心佩经手的各类任务中,她最想不通的是交通文明方面的工作。按照通知,如果学生和家长不遵守交通规则,将倒查到班主任的身上,名曰“动员工作不到位”。学校甚至收集了教职工家属的证件号和车牌号——如果家属违反交规,将连带影响学校的文明单位考核。
不久前,广东湛江的一所小学要求所有学生上下学都要戴头盔,连步行的学生也要戴。看到新闻后的张心佩心里直嘀咕,显然是交通部门的工作甩给了学校,后者干脆一刀切。
“借由老师约束、管理周边所有的人。”张心佩顿感责任重大。
“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,是官僚主义盛行的结果,”雷望红说,“但是后果由基层组织和学校来承担。”
十几年前,山东女孩罗飒飒读初中时,印象最深的一堂课是万圣节那天,英语老师欢迎大家戴面具来学校,罗飒飒戴了一顶南瓜帽和假面舞会的面具。
当罗飒飒成为一名教师后,她热心地向同组老师提议,设计一次有意思的万圣节英语课。对方立刻否决了,“有安全隐患”。
“有很多老师不可控的情况,怕吃力不讨好,没有人担得起责任,干脆‘自我阉割’了。”罗飒飒说。
她还替不配合的家长完成过“其他任务”,否则她会被倒扣绩效;
订阅校服、报纸杂志,也是一级级安排下来,最后由老师承受家长的责问——“你们老师是不是吃回扣了?”
雷望红还了解到,广西某地的老师暑假去家访宣传防溺水工作时,一个家长正忙着打麻将。她请家长在承诺书上签字,家长很不耐烦,你让我小孩代签吧。还有一些地方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,有的群众不愿意交,地方安排学校代收医保,困难和矛盾顺利转移了。
“老师们觉得自己很没有尊严,”雷望红说,“很多事情都跟学习无关,让家长失去了对学校的信任,觉得老师天天在学校不务正业。学校在管理过程中拿什么作为权威资源?”
郑州00后教师自杀事件后,陈瑶的学校下发一封通知,要求教师不得在网络上随意讨论,“更不得随意(凭感觉)对教育内部事宜作评价”。
很快,陈瑶看到网络上其他省市的老师们抱怨,当地立即召开教师心理培训讲座。“非教学任务”又来了——有的要求培训后写千字心得体会,签“心理安全承诺书”;有的说不参加者罚款200元。
有网友评论,这是“雪后再加点霜”。也有人认为,“在这一刻,实现恶性闭环了”。
罗飒飒的周围一片寂静,好像这场悲剧不曾发生过。唯有一天,办公室的一位老教师叹了口气说,“跳楼的老师还是个23岁的孩子”。
然后,就没有人再说话了。
文中张心佩、陈瑶、罗飒飒为化名
1、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,不代表星火智库立场,仅供大家学习参考; 2、如若转载,请注明出处:https://www.xinghuozhiku.com/392870.html